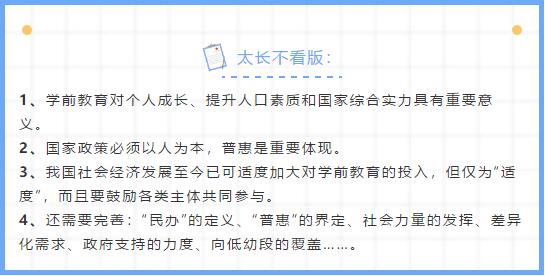学前教育普惠,国家的担当
2020年12月14日
日前,教育部就《学前教育法》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,在条文中释放出一个强烈的信号:学前教育领域,要强调普惠!对此,我个人持百分之百的支持态度,因为这体现了一个国家的担当,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——为民也为国。当然,如何有效地实现这一目标、同时减小负面的副作用,就目前的条文和已有的制度看,还需要不断地完善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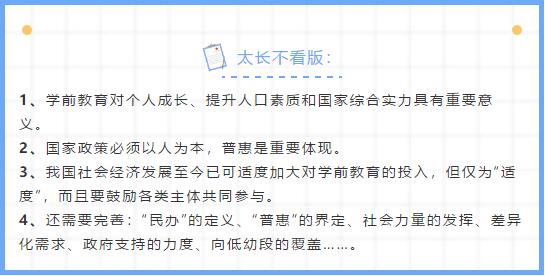

日前,教育部就《学前教育法》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,在条文中释放出一个强烈的信号:学前教育领域,要强调普惠!对此,我个人持百分之百的支持态度,因为这体现了一个国家的担当,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——为民也为国。当然,如何有效地实现这一目标、同时减小负面的副作用,就目前的条文和已有的制度看,还需要不断地完善。